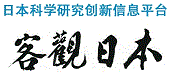受疫情影响,日本部分民众从3月末开始,便自觉不去外面就餐,进入4月以来,日本政府更是将要请餐饮店暂停营业的通知,扩大到全国范围。很多老店、小店、夫妻店仅关店一周便撑不下去,要么裁员,要么转让,要么“顶风”继续营业。毕竟,政府只是要请,并非强制,是否停业全在店主的个人判断。
话虽如此,截至4月20日,大阪府的热线就已经接到了640多个举报电话,举报内容的多数是某某餐厅、某某饭店还在营业。
大阪府吹田市的一家西餐厅,只停业一周便面临破产,店主只好在网站上宣布恢复营业,此后接连收到各种指责的电话和邮件,精神上大受打击。
福冈市南区的一家老店——鳗鱼黑田屋发生了一起具有时代特色、时期特色的挟持人质案。黑田屋是个四层小楼,从大牟田线大桥站北口一出来就能看见。一楼和二楼是店铺,三楼和四楼住着店主一家四口。由于经营困难、食客骤减以及个人原因,店里最近刚刚解雇了一名35岁的男性渡边。
4月21日早上8点半,店主正在做开店前的准备工作,渡边就手持尖刀冲上了三楼,挟持店主的两个女儿,要求跟店主“说说清楚”。经过6个多小时的对峙,警方最终说服了渡边,店主夫妇及两个女儿也所幸没有明显的外伤。
如果不是疫情导致各地政府要请停业,渡边大概还有望找到新的工作,然而在看不到前景的现在,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就成了他疲惫生活的选择。
响应政府要请,自主停业,的确是店主的社会责任,然而店铺的存亡与生活的维系也是店主的个人负担。东京都涩谷的一家颇有格调的烤肉店的门口,放着一张看板,上面写着“助けてください”。这句话可以是“帮帮我吧”,也可以是“救救我吧”。走过的路过的似乎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视而不见残忍拒绝,要么摘下口罩进去就餐。
种种新闻与见闻,让笔者不由地担心起了那家小小的乌冬店,位于池袋乱步路上的“赞岐乌冬”。

店里的桌子是老式学校食堂那种,长长的三条,一条面墙而坐,两条大家对着脸排排坐,一个挨着一个。店主兼大厨兼跑堂的都是一位叫河野的70多岁的先生。
河野先生是“乌冬一筋”,年轻时开店一直干到现在,所以店内依旧保持着开店最初时的风格,非常之昭和,空气里流淌的是收音机里的广播和演歌。现在在日本还肯听收音机的人也是不多了。

面是手擀的,根据上面添加的小菜而设定了不同的价格。放牛肉的就是牛肉乌冬,价格最贵,550日元;放温泉鸡蛋的就是温玉乌冬,500日元;放裙带菜的就是裙带菜乌冬,也是500日元。最便宜的是素乌冬,400日元。也可以另外加钱加料。

汤是用片口鰯的小鱼干熬出来的,由濑户内海伊吹岛上的渔师捕捞后活着送达店里,再由河野先生一条小鱼一条小鱼的摘清洗净,做成鱼干、熬成面汤。熬汤剩下的鱼渣,用手一团,再用油锅一炸,补钙最佳,一团只要30日元。
河野先生惜字如金,与客人的问答极为简洁,也几乎不走出那个一字型厨房。看到客人进门,他就点头示意,说声“来了啊”,让客人自己去厨房跟他点餐,同时付款。客人吃完了,也要自己把筷子扔到垃圾桶里,把空碗放到指定的地方。他会再次点头,道一声“斯密麻森”(译注:不好意思),就仿佛说了 “阿里嘎到”( 译注:谢谢)便会输了一般。

因为距离立教大学比较近,价格又便宜,所以常有一些外地来的苦寒学生到这里吃午饭。对于持学生证的大学生,除了牛肉乌冬外全部有折扣。这其中有一个极为朴素的逻辑,“既然你吃得起550一碗的牛肉乌冬,就算不得穷学生,当然不需要打折了。”
笔者与河野先生,说起来,还是“有过节”的。有一日,笔者点了一碗牛肉乌冬后,又追加了一份牛肉,不料眼馋肚子小,到底是剩下了。改日专门饿着肚子去,誓要吃完一碗牛肉乌冬加牛肉,结果被河野先生不客气地拒绝了。“不能加,浪费”。
不剩饭,不浪费钱,是河野先生不容触犯的底线!

在疫情初期,河野先生的话,似乎多了那么一点点。看到常客来店,除了一句“来了啊”,还会再加一句,“还在上班吗”。当听到肯定的回答时,他会笑一笑,“真挺好”。
这是一个老派男人,能站着就不躺下,停止工作就意味着停止战斗。
如今,立教大学都停课闭校近两个月了,“赞岐乌冬”的近况如何呢?

远远的,笔者就看到店门口竖着一块小白板,不由地心里一紧,待走近一瞧,又是心头一热。
小白板上写着,“好消息,房东出于好心,疫情期间降低房租,我也想将这份好心与大家分享,每周一全品一律便宜50日元,到6月末为止。”——好心与善意,形成了一个正面的连锁反应。

我们都是被迫冬眠的小兽,待到天下大安,还是要走出巢穴,大吃四方的。
供稿: 庄舟
编辑修改 JST 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