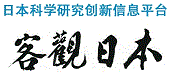狐狸乌冬面与宫泽贤治笔下的狐狸幻灯会
韩国的朋友告诉我,刚到日本时最大的“震惊”是满街的“狐狸乌冬面”、“狐狸荞麦面”等狐狸系类,在韩国作为“狡猾”的代言人的“狐狸”,为什么在日本会与美味料理联姻呢?朋友为“狐狸”这种动物在日韩两国各具不同的定义和身份而惊叹。

日本家喻户晓的“狐狸乌冬面”(示意图)
其实,我也产生过同样的疑惑。那还是在国门尚未对外自由开放的一九七九年,我在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代,还没有健全输送外国出版物和信息的渠道。我有幸得到了宫泽贤治胞弟宫泽清六从日本寄来的宫泽贤治的作品集,并为作品中的 “狐狸”形象所震撼。
震源发自宫泽贤治(1896—1933年)的名作《过雪地》。“大雪牢牢地冻了起来,比大理石还硬,冰冷的夜空就像光滑的青石板铸成”,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四郎和寒子穿着小巧的雪履”,咯吱咯吱地在原野上行走。被两人的脚步声所吸引,出现了一只名叫绀三郎的白色小狐狸。于是,在白雪皑皑的森林中,四郎和寒子应邀参加了由狐狸举办的“跨文化交流”幻灯会,和狐狸们对歌共舞,不知不觉中相互建立了纯朴而诚挚的友情。狐狸们还端出黍膏团来招待他们,却又担心他们是否敢吃。当看到兄妹二人把黍膏团一扫而光后,小狐狸们高兴得又唱又跳——“从此我们不再骗人了”。兄妹二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还收下了一堆板栗作为礼物带回家。这场“异想天开”的双向感应共鸣的联欢会结束之后,小兄妹被狐狸们依依不舍地送到了林外。

宫泽贤治的胞弟宫泽清六赠送给笔者的宫泽贤治作品集
《过雪地》通过孩子和“狐狸”之间的深层融合而阐述了和合的思想、和合的哲理。然而,这一表现手法令我感到意外。因为,这种人物设定和描绘运作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想象。中国的狐狸大都是不受欢迎的反面形象,数千年来一直扮演着动物中的次品。而日本人对“狐狸”的信任度和亲近感也与中国人大相径庭。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キタキツネ物語)在中国上映时也曾引起轰动——其拟人化的叙事手法让当时许多人感叹:原来狐狸不止是狡猾的代表,也懂善意,且有可爱的一面。
相对而言,“狐狸”在中国民间并不具备光辉的形象,在韩国也同样被认为狐狸是奸猾的象征。在韩国,狐狸也是招人厌恶的动物。善于卖弄风情的女人在韩语中被叫为“yo-wu”,即狐狸精的意思。在韩语里,“摆动尾巴”这一说法等同于中文的“飞媚眼”。韩语中的“kumiho”就是指化身为绝色美女的狐狸精,据说她能勾引男人并吸光其精气,从而使自己寿命可达千年之久。
人们之所以容易联想到狐狸的的劣迹,与验证狐狸劣根性的文献不无关联,而这类文献大都源于中国的古典。日韩两国自古以来都浓重的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摄取吞吐过程中也自然接收了“狐狸观”的出没潜入。
因而,当看到宫泽贤治所描绘的孩子与狐狸之间相处水沫相如的场景时,不得不感叹中国与日本对“狐狸”的“料理”效果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与日本虽同为汉字文化圈的近邻,日本自觉主动地选择了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而走向文明的道路,然而仅仅透过“狐狸”观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之间的确存在着似同而异的文化差别。
1981年秋天,我所提交的毕业论文内容是“试论宫泽贤治笔下的动物”。在宫泽的笔下,动物们就像是生活在另一文化圈的生物,它们和人类一样具有同等的智慧和共性,显然,基于这样的定位而展现作品的精神世界是宫泽贤治文学的特点之一。这篇以动物形象为研究资料的论文,没想到竟然成为了新中国第一篇研究宫泽贤治的学术专论。在此基础之上,我不断将宫泽贤治的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在2000年以《宫泽贤治与中国》的研究为题,被御茶水女子大学授予了人文科学博士学位。

笔者翻译出版的宫泽贤治的部分著作
我认为宫泽贤治借用动物想要传递的是,寻求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和谐互鉴,必须具备知己知彼的愿望和姿态。生物与生物、生物与自然,世间万物都肩负尽量减少误读,相互认识和理解的宿命,只有“识天命”,才能维护无限循环的命运链接,那是无法摆脱的共生式命运空间。就这样,宫泽贤治作品中的“狐狸”让我体味到“宫泽贤治的冲击”,极大地刺激了我参与日本社会,研究日本同时也研究中国的好奇心。
日本狐狸观的文化背景
童话作家新美南吉(1913—1943)曾经写过一篇《买手套》的童话。眼看着严冬就要来临了,狐狸妈妈要给孩子买手套,于是便来到了人们居住的集镇。她对孩子说,人类很可怕,并把孩子的一只手变成了人手,告诫孩子说,只能伸出这只手去买手套。可孩子却没有做到,结果被店主人给发现了。幸好店主人很同情这只小狐狸,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照样把手套卖给了小狐狸。这和对九尾狐精心存善意的做法可谓是一脉相承,从中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对动物的温情。
诸如此类,在很多日本的传说故事中能为彼此敌对的双方提供了一个以情相见的平台。从中也可以看到,在日本,动物和人类是被同等对待的。将动物和人都作为“生物”而一视同仁的观念自古就渗透到生活习俗层面了。
在日本,人们还把狐狸视作神的使者——斡旋丰收的稻荷神来供奉。日本全国随处都能看到门口立有红色鸟居(立于神社门前,形似牌坊)的稻荷神社。江户时代的民谣——“伊势店,稻荷院里小狗便”——就是将伊势店、稻荷神社和小狗这三种随处可见的东西并列传唱的。在江户旧城的808个町中都建有稻荷神社。直至今天,日本全国各地的稻荷神社总共有3万多家,约占日本全部神社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民众家里供奉的稻荷神和路边类似于小祠堂一样的稻荷神社。人们公认位于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神社(始建于公元711年)是所有稻荷神社的根据地。

京都伏见大社里口衔稻穗象征丰收的狐狸
对处于农耕文明阶段的古代日本而言,稻荷神是很重要的神灵。同时,稻荷神社还是日本真言宗开山祖师弘法大师(空海法师)所创建的京都东寺的镇守神社。随着真言宗在日本的传播,对稻荷神的信仰也广泛地向各地传播开来。到了室町时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得稻荷神由农耕守护神兼而成为产业守护神、商业守护神,进而被奉为“衣食住的大神,万民富足安乐的大神”。稻荷神的足迹也由农村迈向了城镇,从平民阶层进入到武士上层社会。真言宗对稻荷神信仰的传播可谓是功不可没,而备受真言宗尊崇的荼吉尼天正是自印度骑着一只高贵的白狐而来的。他春天下山,为的是保护农田,秋天则在丰收后才回到山中。人们很容易将其与狐狸的生活习性联系起来,于是对荼吉尼天的崇拜就逐渐演变为对狐狸的尊敬了。正因为如此,位于爱知县丰川市,供奉荼吉尼天的妙严寺(又被称为“丰川的稻荷神社”)受到日本全国信徒们的顶礼膜拜。
自古以来,每当天空中出现半边晴朗半边雨的自然现象时,人们就会认为这是狐狸所施展的魔法,并视之为吉祥的象征,亲切地称之为“狐狸娶亲”。还要举行祭祀活动,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比如在山口县下松市的福德稻荷神社,每年都会为感谢稻荷神带来五谷丰登而举行“狐狸娶亲祭祀节”。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群马县高崎市箕乡町和新泻县阿贺町,每年也都会举行“狐狸娶亲”的祭祀活动。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日本的年轻人竟也还会时常谈论起“狐狸火”(鬼火、幽灵火)。在深山或沼泽,每逢雨后的夜晚,在黑暗中就会飘荡着青白色的磷火光,据说这多少也和“狐狸娶亲”的现象有些关联。在岐阜县飞弹市古川町至今都还每年举行“鬼火节”。
日本人不但愉快地接受了有关狐狸的种种传说,还将其演变成各种节日,为生活增添乐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已经把人和动物之间的互动交流习俗化了,并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的文化氛围中丰富着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狐狸家谱”
让我们顺便简单了解一下源自中国古典的狐狸定位。
据古代文献记载可知,中国也并非从来都把狐狸当成不详之物。《礼记》中就有记载“狐乃仁也”,意思是说狐狸本是有德之物,堪为人类之楷模。《礼记》一书收录了从周朝至秦汉时期的古代礼仪,并据此加以阐释。在成书于秦汉时期的古代地理文献《山海经》里也把九尾狐狸精当成“灵物”加以记载。由曾任秦国宰相的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也把狐狸称为“瑞兽”,其记述如下:“涂山人歌曰:‘悛悛白狐,九尾煌煌,如家就室,倡我都邦’,祈愿为涂山东床”。
但这种对狐狸的好感自汉朝以后就逐渐逆转了。在成书于东汉初期(公元100年左右)的中国最古老的字典《说文解字》当中,对狐狸的注解已经变成了“妖兽”。
整个东汉时期(25—220年)是儒家学说日渐昌盛的时代。此时距孔子开创儒家学说已历经数百年,即便是从西汉汉武帝(前156—前87年)把儒家学说奉为“国教”之时起算来也又过了200多年,儒家的学说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儒家的理论讲究非黑即白,渭泾分明,对人对事都必须基于伦理道德而得出判断,绝不容许不讲原则。于是,对于祸国殃民的九尾狐的印象一经定论就绝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了。
东晋(317—420年)时的志怪故事集《搜神记》(于宝著)中这样写道:“狐狸乃先古之淫妇也”。而作为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中亦写到“狐幻化以惑人”。晋朝(265—420年)是继三国之后,取代魏而建立的统一王朝,但关于它的正史则完成于唐朝初期。由此可以看出,在唐朝时狐狸已然完全被视作邪恶的化身。有关狐狸的传说在唐朝时特别地流行,现在看来都是一个模式,即狐狸精化为美女而坑害男士。
宋朝(960—1279年)的《太平广记》中有关狐狸的传说完全承袭了唐朝的模式。《太平广记》成书于公元978年,是奉旨钦定的鸿篇巨著。全书共500卷,从475种古书中拔粹编辑了包括奇谈、异闻在内的各种传说,在内容上与日本的《雨月物语》(成书于1776年,上田秋成著)类似。而明朝的《封神演义》则沿袭《太平广记》的风格。
白居易(772—846年)的诗中也有“古塚狐,戒艳色也”的诗句,告诫人们不要贪图美色(古塚狐,千年老妖为美妇,容貌姣好,头作云鬓面为妆,大尾曳地化红裳……)。诗歌反映的是化身美女的狐狸精,能让男人们心驰神往,乐不思家,就如褒姒或妲己一般“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所以,“狐狸精”也就成为了“倾国倾城”的魔女的代名词。
清朝的蒲松龄(1640—1715年)更是为狐狸精的形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蒲松龄穷其一生写就了以神仙鬼怪、妖精狐仙为主要题材的《聊斋志异》。这部不朽名著多达120万字,共由431篇短篇构成,其中围绕狐狸精展开的故事实在是不少。但是在蒲松龄的笔下,狐狸们对当时的社会道德观进行了强烈评击和讽刺,从而也对长久以来的狐狸精的负面印象起到了修正的作用。
类似这样的民间传说在韩国数不胜数。由此不难看出,韩国亦深受中国文化中九尾狐传说的影响。实际上,韩国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儒教模范之国”,所以对于九尾狐的印象与中国类似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儒家学说价值体系作用之下的“意外”结果吧。
“狐狸”的形象和特点在中日两国文化中的不同变迁,显示了日本与中国之间文化上的交错与融合形态的多姿多味。是“狐狸”开启了我考察文化交流、文化混合、文化交叉的契机。中日文化的同文可以共同归结到“汉字文化圈”,而中日文化中存在着的相互差异则源于互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之交错。中日间的文化关系像分子与分母,有和也有分。对日本文化了解的越多,越会发现理解的不够深刻,大概 “知”之本身就是对“未知”的一个认识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无止境的文化之旅。具有对日本的调查研究以及生活体验的积累的人都将有所自觉:读解日本的同时,也是读解中国的“双向”过程,是一种自发的“对应的相互探讨”。
因此,援用比较文化的手法对两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生活予以到位的调研与梳理,发挥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之正能量,以激活相互学习的智慧,升腾为相互发展的动力。其成果不仅可以促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双方各自的自我反思,温故创新。
文/图片:王敏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