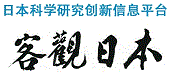L.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1928年出生在与荷兰接壤的法国北部边境。母亲是城里人,父亲土生土长,乡音里夹杂着荷兰土语。父母口音的明显差异使他从小就对语言十分敏感。从少年时期开始,汪德迈除了母语法语以外,还掌握了德语、荷兰语、俄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后来随着对东方的关注,他开始接触并逐渐学习掌握了汉语、印度语、越南语、韩语等亚洲语种,并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中国研究与亚洲研究。1951年,他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先后在越南、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等地执教。1975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法国的博士学位原分为三种,国家博士、第三段博士 (doctorat de troisième cycle)和大学博士(doctorat d'université)。国家博士为法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1984年法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取消三种学位,统一为博士学位(doctorat))。

在汪德迈先生故乡的餐馆。前排左一为汪德迈先生,右一为笔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汪德迈在亚洲从事了40多年的考察研究,期间他先后三次赴日留学、任教与任职:1959年~1961年,在同志社大学留学;1964年~1965年,担任京都大学客座教授;1981年~1984年,出任日本法国文化会馆馆长,前后六年的日本生活成就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累累硕果。
汪德迈荣归故里后,基于其研究亚洲各国的丰厚成果,起初在巴黎第七大学执教,而后又于1973—1979年赴任巴黎大学,1979—1993年活跃在巴黎高等学院的研究最前沿,1988—1993年被任命担任法国学术顶峰・远东学院院长和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
汪德迈与日本
汪德迈的博士论文《王道》上卷完成于1977年,下卷完成于1980年。1986年出版的《新汉文化圈》(日文『漢字文化圏の時代』、大修館書店出版、1987年),是对其博士论文中最精华部分的拓深,也是利用日本的研究成果在驻日其间脱稿的杰作。
2016年9月和2017年2月,我有幸在北京和巴黎先后两次对汪德迈先生进行访谈,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汉字文化圈予以的期待,对西方文化寄予的建设性意见,以及对汉字文明前景的热情希冀。其间,汪德迈先生多次发出感慨说:“我的亚洲研究、中国研究以及汉字研究的契机始于留学日本”。

笔者在汪德迈先生的巴黎寓所采访
汪德迈回忆说,学生时代对于日本的了解和认知很少,只知道在二战中作为侵略国家而出现的日本在地图上的地理位置。1951年,他前往越南赴任,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造成的罪恶,给被侵略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难以消除的苦难。所见所闻使得他难以对日本产生好感,甚至一度拒绝接受法国指派自己赴日留学。
最终,他还是不情愿地接受了赴日留学。在日本留学与生活的日子里,日本民众朴实的民风民俗改变了他对日本的看法。自幼就对语言充满兴趣的学术好奇心由此发生了质的转化,使得他对于日语与越南的喃文、韩文、中文的共同点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兴趣,决意投身这些区域的语言之源头——汉字与汉学的探究。从此,汪德迈明确了目标,将研究课题聚焦在汉学、中国学、亚洲学的根基——汉字领域上。
虽然日本是决定汪德迈学术研究方向的主要舞台,但是最初引领他进行东方学术研究的是戴密微教授。戴密微(1894~1979)曾执教于瑞士、法国的东方学重镇——巴黎东方文学院,从事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汉诗翻译,担任『T'oungPao』主编长达30年之久。正是戴密微推荐他到日本留学的。
结束两年的日本留学之后,戴密微指定汪德迈奔赴下一个深造场所:香港大学。于是,汪德迈于1961至1964年寄宿在国学大师饶宗颐(1917--2018)家中,师从绕宗颐专攻中国古文字学和语言学。饶宗颐曾任香港大学校长,被世界公认为汉学研究的泰斗,“中国的国学大师”、尊称为“东方的列奥列娜・达芬奇”。
汪德迈告诉我,他有三位“终生的恩师”。第一位是巴黎东方文学院的戴密微教授,第二位是日本的恩师、同志社大学的内田智雄(1905—1989)教授,他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制度史、法制史的专家。第三位就是饶宗颐先生了。
正因为汪德迈对日本怀有情真意切的师承渊源,所以才在《新汉文化圈》中毫不掩饰地指出:“希望日本意识到身为汉字文化圈最前沿的定位与责任”。但是出自对于日本的深厚感情,他也感到忧虑和不安。在巴黎汪德迈的家中,他曾心思重重地对我说,“当前日本的治国理政顺序值得斟酌”,“从社会发展的优先顺序来看,比起政治和经济先行,是否应该优先提高文化方面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准”?
关于中日关系,他反复强调“日本只有与中国保持和平,才有希望。近年来中国在文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日本应该把它理解为是一次良机,积极参与、积极配合”。
谈到日本文学与汉学,精通日语的汪德迈说,他最爱读的书是夏目漱石和小泉八雲的作品。他评价这二位的创作是把心絮捧在掌中,呈献给读者。在学问方面他最尊敬白川静、吉川幸次郎等日本汉学家。
通过与汉字文化圈的比较,汪德迈针对西方发展停滞的状态,提出了应该借鉴日本做法的两个建议。第一,西方过分偏重个人主义,亚洲共同体精神及其生活方式应该成为西方的参照;第二,西方个人主义的合理性通过法律得以强化,而亚洲尤其是日本式经营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处理,尤其是重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纽带作用,这方面可引以为鉴。
他认为,“亚洲人在努力地理解西方,西方人也应该付出同等的努力回应亚洲”。这是汪德迈一贯的核心主张。
“新汉文化圈”的范围与经济增长
1986年,汪得迈的专著《新汉文化圈》法文版发行。第二年该书就被翻译成日语,1987年由大修館書店出版了日译本《亚洲文化圈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旗手——》(日文书名『アジア文化圏の時代―政治・経済・文化の新たなる担い手―』、福鎌忠恕訳)。直到2007年,中译本《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陈彦译)才正式出版,中译本的问世比日译本晚了整整20年。
汪德迈定义的新汉字文化圈的范围主要设定在中日韩和越南。《新汉文化圈》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序论部分概括了汉字文化圈的过去与现在。第一部分阐述经济状况,分析了汉字文化圈所迸发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活力,及其所具有的同一结构型经济发展走势。第二部分剖析了政治局势,提出中日关系的和解与紧密化附合民众的意愿;朝鲜半岛诸问题必将朝着协调的趋势发展;中国与港澳台将再次统一;中越间的危机关键在于中苏关系。第三部分探究了汉字文化圈共同拥有的最美好的媒介——汉字,汉字的集大成儒学与传统文化必将振兴光大。结论部分指出了新文明形态,即新汉字文化圈的出现与其构造。
综合汪德迈提出的“新汉文化圈”主张,大致可简约为:汉字将成为公共使用的最佳媒介,通过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乘经济发展的强劲走势,势必汇集不同区域的文化和力量,相向而行,在亚洲共筑新型文明形态。它将突破欧洲曾经参与制造的与东亚的敌对关系,按照汉字文化圈各国国民自已的意愿,向着和解合作的方向前进行。
汪德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根据1974年的日本数据资料和日本经济企划厅统计得出的1961~1981年世界国民生产总生产值,得出了除越南之外,汉字文化圈的经济增长位于世界前列的结论。此外,还明确指出汉字文化圈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获得了近一倍的增长,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称赞的发展成果,日本的贡献功不可没。
具体来讲,汪德迈发现,“如果根据1960~1978年期间的亚洲各国的增长率的顺序来进行分类,不难发现,隶属亚洲即汉字文化圈的国度位于前列”(《亚洲文化圈的时代》5—6页)。也正是这种排列启示了汪德迈,不妨将共享汉字历史文化的区域视为新一轮的“汉字文化圈”,对该范围内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抽样与整理。
那个时代尚没有从汉字文化圈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视角,更缺乏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重点分析的意识。因为当时习惯于将同一水准的国家进行平面排列的惯用手法。于是,中国等国家便被划分在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数值高的日本被划分在发达国家的范畴。然而,如果以“汉字文化圈”为独立的范畴进行考察和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此基础之上,将近30年来汉字文化圈内主要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欧洲各国的停滞状态显而易见。
当时的欧美被认作经济发展的固定模式。汉字文化圈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完全采用与欧洲同样的方法和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状况,汪德迈在著书里列举了日本的成功范例,比如公司食堂、集体旅游、同乡会、终身雇用制等等。他认为这些制度和形式体现出共同体的精神,也反应出汉字文化圈所共有的特征。当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只有汪德迈。
汉字的本质
在欧洲的汉学家眼里,汉字文化圈有两个最大的特征:“使用筷子”和“使用汉字”。汪德迈认为汉字文化圈的相似性源自汉字的本质。
根据近60年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汉字的雏形——甲骨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所具有的“创造”性“思维”与“活力”所致。正是这种思维与活力历经数千年的流转,不间断的催生出文字的演变再生。例如,伴随着王朝和时代的变迁,汉字的书写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现代汉字、繁体字、简体字的变化,那是因为潜藏在汉字中的“创造”要素和活力的传承始终未变。
为了验证这一点,汪德迈详尽地研究了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的各个阶段的演变,断言“汉字所具备的特性不会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并且据此推理,中国经济从长期的停滞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爆炸型增长的“秘诀”,也可以认为与汉字同体的创造性和活力息息相关。只要汉字尚存,其间源源不断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力就不会停滞。即使历经长久的冬眠,那潜在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力的根源,必定适时而生,进而复苏,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有机互动。对于汉字本质的探究也是汪德迈联通新汉字文化圈与经济发展之关联性的研究过程。
汉字的功能
汪德迈认为,汉字作为一种文字,兼具音、形、意三个层面的功能。例如同一个汉字可具有不同的发音。即使音与意的分离,使得人们无法进行顺利的口头交流,但是却无法阻碍书面的交流与传播。所以,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汉字作为共同的交流符号具有相互融通的功能。孙中山与日本的交流就是发挥了汉字笔谈的效果。以日本为主的亚洲其他国家之所以引进了汉字,也出于认识到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可望运用“书同文”来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
汉字更深层次的作用是承载了富于创造性的价值和理念,比如儒、道、仁义等。这些理念通过汉字来传达,成为连接汉字使用地区的智慧纽带。汉字作为一种文字,可以剥离语音而存在,这一点是思想传承中最根深蒂固的能量所在。
汉字之所以可以剥离语音而存在的要素是象形功能。观其形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知其意。例如,“雨”字就是这样,人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图画。现代人借助相机和影像才得以可视化的事物,其实早在遥远的时代就已经被汉字予以实现了。汉字在各自具有独立意义的同时,还可以和其它汉字组合成新的意思。例如,活+力的组合就成了“活力”,任何汉字都具有生产出新词汇的创造功能。所以学习汉字,是认识中国价值和中国人思路的捷径。了解汉字的作用和本质,有助于认识事物和构置思想、铺垫逻辑。这也是汪德迈通过检验而确认的汉字文化方法论。
文/图片:王敏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