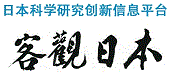春日大社里的鹿、熊野神社里的乌鸦、稻荷神社里的狐,都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宗教符号。
稻荷神社在日本各地皆有,公园、小巷、甚至是某大公司的天台上。因此,红色鸟居和狐的配套最为多见。据统计,日本的三万多家稻荷神社里,都有狐的石像或铜像,而且嘴里往往都衔着东西,比较常见的是稻穗、钥匙、宝玉和书卷。

稻穗象征着五谷丰登,钥匙和宝玉象征着稻荷神的御灵,另有一说是象征着天与地、阴与阳的万物创世之理。书卷则象征着民间对上天的请愿书。
古代日本人认为,凡人直接向神寻求帮助是大不敬,需要一种灵兽做人与神的信使,把人的愿望转达给神。而狐的尾巴呢,看上去就像金黄色的稻穗一样,所有能与稻荷神相通。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兴起,日本还出现了神佛习合的现象,也叫神佛合一。稻荷神被当成是印度密教里的荼枳尼天,其习性与狐相似,其座骑又恰是一只白狐。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公式,稻荷神约等于荼枳尼天,荼枳尼天约等于狐,稻荷神也就约等于狐了。
到了江户中期,稻荷神的信仰越发隆盛,商人把他当做“买卖神”,武士们把他当做“镇屋神”,农民们把他当作“部落神”,稻荷神社也从此遍布日本大街小巷,狐假神威得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拜狐现象并非日本独有。中国在唐代也流行过天狐信仰,认为天狐“奉天职”,可以出入天庭,属于“天上神”。到了清代,狐仙信仰和狐仙崇拜在千余年来的承袭中到达了巅峰,关于狐仙信仰的文字记录颇多。

康熙年间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乾隆后期有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乐钧的《耳食录》,光绪年间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李庆辰的《醉茶志怪》等不胜枚举,三百年间狐仙之谈不绝于书。
创作离不开生活,小说是研究民俗的重要史料和依据。清代狐仙信仰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地大建祠庙进行祀奉。所谓“南方多鬼,北方多狐”,以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地最盛。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的都总管庙就是狐仙庙,所祀的“狐总管”乃是全国狐仙之首。
不仅民间,就连官署里也开始堂而皇之地供奉起了狐仙。《遁斋偶笔》中记“大同学使院设酒果以祀”;《新齐谐》中记“严秉介作云南禄劝县,县署东偏有屋三间,封锁甚严。相处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庸庵笔记》中记“宁绍台道署署后有小屋供财神,其旁塑白发而坐者三人,询之旧吏,乃云狐也”;《客窗闲话》中记“浙人章生,应台湾省之聘,见岑楼三间,为狐仙供奉之所。”

据说,这清代官署供狐仙,是有其特殊目的的,或借狐仙法力看守文书,或借狐仙法力以守官印。
中国的狐仙也有派别。冯梦龙的《平妖传》、唐人戴孚的《广异记》、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清人梓华生的《昔柳摭谈》里都谈到,“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
男狐呢,则偏爱姓“胡”。钱钟书将狐仙之嗜读好学的特色,称之为“胡氏家风”。日本民俗学者吉野裕子也曾在著作《神秘的狐狸》里,提到日本《提醒纪谈》中有两只学者狐狸——幸庵和蜕庵。幸庵常以佛理教谕他人;蜕庵善占卜,知吉凶祸福及将来之事。这些日本的学者狐狸皆源自中国的“胡博士”。
至于日本民间的拜狐现象,与唐朝以来的中国民俗有多大关联,这许多年来也很难正本清源。更有传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就是由从中国大陆到日本的“渡来民”,也就是移民秦氏一脉创建,日本自此便开始拜狐。
供稿: 庄舟
编辑修改 JST 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