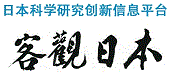体内的生物钟告诉我,应该是早上了。
虽然彻夜难眠,但还是看了看表,昏暗中使劲张大眼睛,已经六点了。本以为一切都是梦,但是陌生的天花板告诉我这里不是我的家。环望四周,妈妈躺在对面的床上。雪白的床单和被罩提醒我这里是旅店。
其实也没花多长时间,一切记忆又涌回了大脑。
是的,在这铺床榻上,我挨过了17年来最难过的一晚。昨天在日本大使馆的楼下,等待办理签证的时候把所有资料都弄丢的场景历历在目。侧目看了看妈妈,想必也是一夜没睡吧。本想说些什么的,可是干裂的嘴唇让我感觉到了一丝丝扯痛。痛感是很现实的,又一次将这不是梦的事实,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通过神经报告给了大脑。没吃没喝到现在,奇怪的是丝毫感觉不到饿意。
妈妈也已经坐起来开始整理东西,地下室的灯光,不是很亮。隐约能看得到妈妈红肿的双眼。
“妈,饿不饿?”我的声音低到自己都有点听不到。空气中弥漫着我懊悔和抱歉的情绪。
妈妈也只是摇了摇头。示意我去叫我的同学,说人家一直跟着帮忙找东西,怎么也要请人家吃早餐。
走出地下室,天亮了。三个人在“地上”汇合。商量去哪里吃早餐。已经有12个小时空腹了,胃袋居然没有跟我示威它现在的“贫瘠状态”。
“走吧,吃完饭去火车站看看能不能买到回去的票”。妈妈边说边往外走。我又一次背上了我的黄色单肩包,出奇地沉,宛如我跌倒谷底的心情一样。
没走两步,朋友的BP机响了。我没多加想,脚步紧随着妈妈。可能是因为在地下室的关系,旅店里一直没有信号,消息这时候才传来吧。

传呼机和公用电话亭(图片源于网络)
“这是不是你家的座机号?”身后传来朋友的声音。看着这一串熟悉的数字,估计爸爸也是在家里担心了一个晚上吧。丢完资料后跟爸爸联系之后,在派出所报完案后也忘记给他打电话了。当年,公用电话亭的普及率还是很高的。沿着马路走了十几米,就有一个。跟朋友借了IC电话卡,我拨通家里的电话。爸爸的声音依旧那么地深沉且有包容力。还没等我把昨天的始末讲出口,爸爸就急切地问我有没有笔和纸,让我记一串号码。一边担心长途电话会不会将电话卡里的钱都耗尽,一边手忙脚乱地翻出笔和纸记了下来。
“我从昨天半夜就开始给你同学打传呼(BP call)”爸爸说。
是的,我和我妈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一直也没回信,就等到现在”。爸爸继续说道。
“我们住了个旅店,是地下的那种,估计是没有信号吧”。让您担心了,在心里默默补了后面一句。
“昨天晚上快十二点的时候,有个人给咱家打电话,问是不是安宁的家。说是捡到了你丢的资料。”爸爸几乎是不喘气地说完后又接到:“说是先给你日本学校驻北京办事处打了电话,但是都已经下班了。然后翻看里面的材料才找到咱家的电话号码。”听着听着我明显感觉到我握着听筒的手有点发抖,甚至从昨晚持续到现在的头痛在那么几秒钟之内神奇般地消失了。那种滋味我自己觉得绝对应该是与孙悟空拿掉紧箍咒后的感受是等同的。
这时妈妈也凑了过来,应该是担心发生了什么事吧,但我来不及解释,虽然我很想很想大声地叫出来。但为了仔细把爸爸的话听完而忍住了。
“刚才那个号码,是捡到的那个人的BP机号码,你联系他一下吧。然后,好好照顾你妈”。在爸爸简单的几声叮嘱之后,我挂断了电话,望向妈妈。她用眼神示意我赶快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用明显提升了一个八度的声音,将有人捡到我的证件的事情跟妈妈和朋友讲了一遍,一口气下来,我差点窒息。
就在同一个电话亭我拨打了对方的传呼号。接通后,我将自己的姓名和留言转告给了接线员。几乎祈祷式地放回话筒。站在一步之遥的距离等对方打回来。(不太懂BP机用法的朋友请自行查询)
三个人六只眼,眨呀眨,有默契地屏息等待,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马路上的吵嚷声都被我们用意念自动降噪生怕听不到来电的铃声。
“铃……”
反射性地将朋友推到电话机的前面。自己实在不敢去接。朋友也是反射性地拿起了听筒,生怕下一秒铃声就会断掉一样。有那么一世纪之久的感觉,朋友谈话结束转过来跟我们说:“是个男的,说在一个叫做肖村的地方。让我们到XX家具城前面下车后再联系他。”
“他还说什么了吗?”妈妈急切地问道。
“就问了你们一共几个人之类的。还问我是本人吗?”朋友回答到。
站在一旁的我很明显地听到了一声来自自己肚子“咕……”的动静,而且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接二连三的咕咕叫。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好饿!
还是办正事要紧,我们决定先去拿资料后再吃饭。妈妈没有丝毫犹豫,抬手召唤了出租车。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只要不出市外,打车费均为五元,北京的物价其实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是有些贵的。然而看到这么果断的妈妈,莫名感觉她的背影又高又大。
司机是个很和善的人,用地道的北京腔寒暄着问我们从何而来要办何事。妈妈坐在副驾驶座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肚子的咕咕叫也一直没有停,附和着司机爽朗的笑声充满了车内。应该是妈妈跟他说了我们的“遭遇”吧。司机先生也是很直快地说道:“也有可能会跟你们要一些好处费,这都没准儿”。妈妈也附和着说:“是呢。不过要多少钱我都要给啊,没办法。能找回来就已经阿弥陀佛了”。我和朋友对视了一眼,毕竟对于还没走上社会的我们来讲,一听到有关钱的事情还是会很紧张和有压力的。
伴随着司机先生的一句“就这儿了,到了您呐”。我望向车窗外。这里应该是正在开发的地段,空旷但又很整洁。工地用的沙子在远处堆成了好几个大坝式的“山脉”。我和朋友在周围寻找公用电话亭。偶然间瞥了一眼妈妈,看见她偷偷地数着腰包里的现金。应该只有那么0.1秒的时间,我的眼泪挤满了眼眶,胀得有点酸痛。她一定是在数剩余的钱有多少,计算着要给对方多少谢礼,又留多少钱买回程的火车票。在我努力控制情绪的时候,朋友已经驾轻就熟地拨通了对方的传呼号告知我们已经到了。
大概等了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看见远处沙子坝上的三个人影。虽然有点远,但是不难看出他们是在一边走一边吃。松软的沙地让他们的步伐有些踉跄。我心里想:之前问我们一共几个人所以你们也是三个人过来的呀!这是要谈判的架势啊!
距离稍微近了之后,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我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牛皮信封了。被夹在领头的人的右臂里,左手拿着热乎乎的包子在吃。身后的两个人也是一人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类似的早餐,三个人均穿着工地工人的服装。应该就是他们了。我一个箭步迎了上去。刚走到“坝下”,他们已经到达了“坝顶”了。已经能闻得到他们包子的香气了。
“你叫安宁吗?”对方先开了口。
“是的,您好。听说您捡到了我丢失的材料,谢谢您”。我小心翼翼地回答着。
“你爸妈让你出国真不容易呢,以后要多注意点,不要再丢东西了。”对方又说到: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缺什么证件”。随后把牛皮信封递了过来。因为地势的关系,我是属于仰望着他的姿势。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柔和的阳光并不是那么刺眼,从他的背后照射过来,仿佛他站在一个光圈里。一瞬间,有点佛祖下凡来教训我这个毛躁小屁孩的感觉。
双手接过稍微沾了点油渍的牛皮信封。但还是平整的。妈妈在一旁忙着感谢,我则是有些激动地查看信封里的证件以及材料。完好无损,都在! 翻开护照,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女生在朝我微笑,仿佛在跟我说“我回来咯”。

妈妈很用力地想塞给他一些钱,但是对方也一直拒绝,说“大姐,真的没有关系的,你们供一个留学生不容易,心领了”。那时那刻,那一幕,虽然自己是整个事件的主角,但又仿佛站在圈外看了一场电影。
初春的阳光和煦而温暖。妈妈擦了擦额头沁出的少许汗水,领着我们又一次鞠躬道谢。随后我们便离开了那个逗留了不到二十分钟的地方。
回程的路上,妈妈开玩笑说一夜之间长了好几根白头发,让我负责。我说:“好!回去以后给你买黑芝麻……”。
妈妈开怀大笑,没觉得我的回答有多么幽默,只记得妈妈笑了好久,好久……(未完待续)
供稿:安宁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