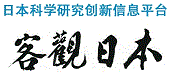上接: 我的日本留学路(一):放弃北京某大学,突击日语拿签证
那是17年前乍暖还寒的三月,正处豆蔻年华的我在妈妈的陪伴下,从内蒙的一个小城市乘坐绿皮火车来到了首都北京。是的,经过多方努力和筹备,我留学去日本的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接到日方寄过来的入学通知书的时候,终于对这件事有了真实感。很轻很薄的一张纸,放在手心里却感觉很沉很沉,欣喜地读了好几遍,那个红彤彤的印章在太阳的照耀下格外耀眼。

这是我多年后再次乘坐的绿皮车
当然光有入学通知书和邀请函是不够的,最让人紧张的不外乎是签证。这几个月所有努力办理的资料都要提交给日本大使馆,最终使馆方根据材料来判断是否签发去日本留学的“入门证”。
出发前的晚上,我郑重地将确认了不下十遍的资料装进了一张牛皮信封。对于当时的我来讲,牛皮纸袋莫名地有种仪式感,感觉自己像大人一样在“办大事”了。
将两人份的随行物品放进了一个浅黄色的单肩包,在贴近身体的那侧,牛皮信封静静地“站在”那里——我特意竖着放的,怕资料压出褶皱。现在已记不清是谁送我们去了车站,怎么上的车,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北京西站下了车。我单肩挎着包,跟在妈妈的后面,随着人流一路走到了地铁站。妈妈应该是在火车上打听过的吧,脚步虽然很快但是背影看着很从容。之后我们先后辗转了地铁和公交,没记错的话是在三元桥下的车,来到了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所在地。
这个被称作南银大厦的高楼,在那个初春的中午显得格外地耀眼。炽热的太阳将光芒毫无吝啬地洒在这个满是玻璃的建筑上。在那个年代,周围的高层建筑还是很少的,尤其是站在楼底仰望的时候更显这座楼的巍峨。

南银大厦
咨询了办事处,得知要分批进入,一次只能进入30人左右。我被分到了下午两点半的那一组。看了看手表,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找个地方等一下吧。环望四周,这才发现楼外面的绿化是很美的,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与迎风飘扬的万国旗交相辉映甚是好看。绕着楼一周,有很多长方形石凳供人休息。选择了一个背朝高楼面向大街的石凳坐下。将手里的牛皮信封放在了自己和妈妈的中间,随后也把背了大半天的单肩背包放在了上面。稍微舒展了一下筋骨和妈妈对视了一眼,不言而喻地轻松。看着街上形形色色的汽车和行人,很多都是叫不上牌子的。在我十点钟的方位有一个公交站点,有很多貌似打工族的年轻人在排队。巴士来一趟拉走一群,几分钟后又排了很多人。不知道看了多少趟公交车来了去,去了来。不经意间看向妈妈,在太阳的炙烤下她的额头沁出了些许的汗珠。
虽然我和妈妈是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但在那个敏感的年龄段我很少会说出关心妈妈的话。与绝大多数处在青春期折腾的同龄人一样,总是有种“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固执和傲娇。现在想想估计是觉得自己马上要出国了,不能待在妈妈身边的一股情愫作祟吧,我建议妈妈去那个公交站点的椅子上坐坐,因为那里可以暂时躲避太阳公公那得意而耀眼的“笑”。目测距离也就二十米。妈妈答应了,我们起身来到了公交站点亭下的阴凉处。顿时身上的燥热平复了许多。正在得意让妈妈远离了“受罪”的我,被妈妈的一句话惊醒:
“信封你拿着呢吗?”
“你没拿吗?”我声音开始发抖,然后本能地回头望向几分钟前我们还坐着的石凳,光滑的石凳上空无一物。此时此刻我多希望一向引以为傲的2.0的视力是假的,让我看得不是那么的清晰,一眼就看见那个信封不在石凳上。一定是刚才起身的时候我只拿了包却遗忘了在其底下的信封。
虽然是很近的距离,我拼尽全力跑了回去生怕再晚一秒钟信封就会离我们更远。然而现实并没有让我们的故事发生转折。旁边的石凳上坐着一位男士低头在看书,尽量不想打搅他午后阅读的美好氛围,努力抑制自己焦急的心情问道:“先生,您有看到这个石凳上的一个牛皮信封吗?” 他摇了摇头。之后又问了好几组周围的人,都说没有看见。只有一个人说好像有一位男士在我们离开之后坐下了,在看一个信封随后便走掉了......
“谢...”,另一个谢字已经消失在我飞奔的途中。
大脑完全是懵的状态。记不清自己绕着南银大厦跑了多少圈,问了多少个人。那种感觉很奇怪也很不舒服。大脑已经罢工像是在刻意逃避这件不该发生的事情,跟人说话时自己听着都有回响。也问了大楼讯息处,一个年轻的小姐姐用对讲机帮我跟所有的工作人员问有没有人捡到信封的时候,等待回信的那十秒钟我幻想了无数次听到肯定的答案。但结局是,谢过一脸抱歉和担忧的小姐姐,继续跑……
当我再次跑到南银大厦入口处时,已经有二三十个人排队,按照保安的指示缓缓进入。是的,如果没出这个意外,我也应该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看了一眼手表,两点三十分。本以为我会掉眼泪,结果一滴也没流,一定是太阳烤的再加上一直跑导致身体里的水分都被榨干了吧。
很无助很无助,妈妈也在周围树木丛中仔细地找着,看到稍微有茶色的东西都会反射性地用视线扫一下。妈妈心脏不是很好,我真的怕她在这里倒下。渐渐感觉到了两个人力量的局限性,我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联系了在北京认识的唯一一个高中同学。一个多小时后朋友从大学校园风尘仆仆地赶到,手里攥着一厚沓“寻物启事”和一卷胶带。一定是恐慌值过大将脑内的感情中枢短路了,以致于忘了说声谢谢,就争分夺秒地开始在周围张贴并打听消息。

南银大厦绿化带(图片取自网络)
不知不觉天也暗了下来,能见度变得很低。三个人一下午连口水也没喝。一无所获地又聚在了南银大厦的楼底。在还算“头脑清醒”的朋友的建议下我们选择了报警。人生第一次坐了警车,还是朝阳区派出所的。警察首先安抚了我们的情绪,但是又很委婉地道出:“虽然知道你们很着急,但是如果是自己弄丢的东西是不能立案的。你们只能备案登记一下,如果有好心人捡到了会通知你们的”。虽然警察叔叔极力温柔地表达着,但一字一句,还是硬生生地将刚刚浮现的希望 “扼杀”在了水面下。
走出朝阳区派出所,晚上六点的北京已是万家灯火。突然感觉北京好大好陌生。身体的疲惫加上精神上的打击,已经完全迈不动步子了。朋友又很贴心地打听到,就在派出所的旁边,有个地下室旅店,花了20还是40元订了一间房。躺在床上,隐约能听到妈妈自责的哭泣声。我依旧没有眼泪,两眼放空就那么躺着,没有开灯也看不到天花板,但我仿佛能看见那个我检查了不下十遍的牛皮信封……

日本小学馆(出版社)大楼前的多啦a梦(照片:客观日本编辑部)
如果真的有多啦a梦的时间机器,我挺想穿越回去看看当时的自己,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的自己,是狼狈还是坚强,亦或是有了更多的领悟。我要不要抱一抱那个精疲力尽地站在南银大厦楼底的她,要不要拍拍那个望着地下室的天花板却哭不出来的她。打住!最重要的提醒她起身之前不要忘记牛皮信封才对。
第二天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会在下一篇连载里和大家分享。
供稿:安宁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